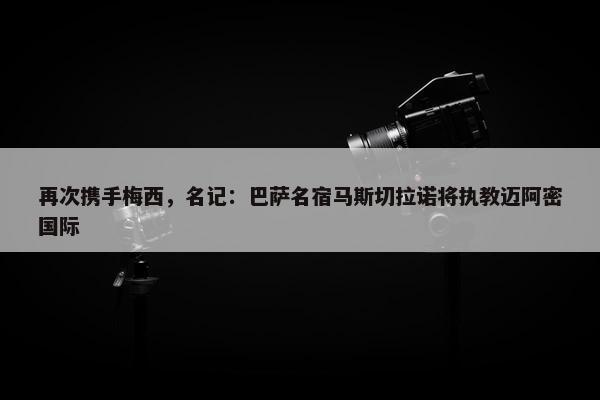小鹿:我希望自己因为好笑被人记住
喜欢模拟经营题材游戏的玩家,对《冰汽时代》这部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了,11bit studios在18年发售的初代《冰汽时代》时至今日依旧特别好评,玩家们在末世后的冰雪环境下建设自己的城市,人性的考验与城市的扩张,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着城市居民的性命以及自己的地位。鉴于初代作品的大火,11bit studios也沉淀了6年的时间开发...
2024年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 期,小鹿穿着婚纱上台讲脱口秀,主题吐槽就是几个月前自己的婚礼。资料图
2024年,脱口秀演员小鹿完成了几件人生大事。 件事就是与外籍男友结婚了,办了两场婚礼,步入婚姻生活。她脱下西装,穿上婚纱登上喜剧综艺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的舞台,对婚礼的吐槽变成一个个喜剧段子,让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决赛,并最终获得亚军。
好友、脱口秀演员周奇墨评价2024年重新出发的小鹿,“打出了一种气势,谁都接不住”。2014年小鹿 次登台讲脱口秀,2021年,身为律师的她注销了自己的律师证,成了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。
脱口秀演员刘旸表示,小鹿以前给他的感觉是“过于认真严肃”,如今,“她玩起来了,写的东西太炸了”。对于周围人的评价,小鹿表示,所谓的转变是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。以前在台上故意不笑,严肃地讲东西,那是她本身喜欢的脱口秀风格,“我就喜欢穿着西装,装成大人模样,讲一些很荒谬的东西,这个反差感本身就很喜剧”。后来观众看她穿西装,会不自觉地有点紧张,“本来穿西装是为了加强喜剧效果,结果削弱了,那我就 了。”她说。
南方周末与小鹿的专访约在了10月14日深夜。她已经结束了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的表演,没有休息两天,就火速投入了个人专场的准备中。小鹿是高频出现在各大开放麦的脱口秀演员。“这就是脱口秀演员的常态——讲段子。我们上开放麦就像上班族每天上班一样,我们是白天写稿,晚上去开放麦,可能大家是白天上班,晚上休息。喜剧是很科学的,观众没笑,这个段子就不行,所以就得不断找观众试练。”
脱掉西装后的小鹿,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。“我 坚定的事情就是,我真的很努力地在喜剧能力上精进自己,因为我从一开始上台就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好笑的人,因为好笑被人记住,被人喜欢。”她说。
以下为小鹿自述。
笑点这种东西,像我脑子里的后台一直开着,生活中我就不经意去捕捉。
像我今年决定从北京搬到上海,在上海找房,就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比如中介可能想告诉你这个房子比较西式,一定会打一个括号,写着:老外刚搬走;再比如汤包(编者注:小鹿老公)去找房,明明两个房子之间隔得很远,中介非要跟汤包说一会儿就到,汤包 次跟他从A房到B房,他说很近,就六七分钟,结果汤包跟他骑了35分钟的自行车。
再比如今天有人来我家看房子,我北京租的房子,是胡同房,他问会有老鼠什么的吗,我说偶尔会有吧,有些地方没封好。他特别认真地说,哎呀,那老鼠会咬到我的小猫的,算了,算了,然后就走了。
再比如,我现在和你聊天,边上汤包正要出去扔 ,我就看他表情 诡异,后来发现他找不到自己的拖鞋,就把他44码的脚塞进我38码的洞洞鞋里,他竟然穿着就出去了,还是高跟鞋,太荒谬了。
你说我对生活有敏锐度,我也不太自知,但是我从一开始上台讲脱口秀,所有的一切发生,都是基于我喜欢在台上逗人笑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就是一个特别希望自己变得好笑,并且努力去变得好笑的那种人。
我还记得我 次上台,是拿着纸上去的,因为我记不住。我当时刚学着写段子,就是典型的预期违背的段子,一个铺垫,一个反转,观众是一定会发笑的,可能就给我建立了一种信心。而且我运气特别好, 次上台开放麦,演完马上就 次商演了。
我要给你发一张我 次演出的照片,那时我刚来北京,120斤左右,是我整个体重的巅峰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胖,外形上也很普通,那时候我还没有摆脱审美对我的压迫,而且在人群中站着,是啥都不出众的一个人。但是我来北京做喜剧后,我站在台上逗别人笑,发现根本没有人在意我的外形,只要你的东西是好笑的,别人就会喜欢你,观众透露出来的善意,就是一开始喜剧舞台最吸引我的地方。
还有一点,从这张胖照片能看出来一个女孩子成长蜕变的过程。很多人会觉得18岁真好,老天爷啊,18岁我一点都不想回去!我觉得现在真好,现在每一天都是我想尽一切办法才成为了的自己,我才不要回到18岁,又得卷土重来。
2014年,小鹿 次登台讲脱口秀时的“珍贵历史画面”。受访者供图
我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,哪怕是事业上的一些挫折,比如我之前参加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“一轮游”,后来参加《脱口秀大会》反复被淘汰,尽管事业上会有一些挫败或者什么,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不管怎么挫败,每次去开放麦见到观众,跟他们讲段子,他们开心,如果有些我特喜欢的东西他们也能get到,我就觉得好爽。
脱口秀演员讲段子,基本都是这么一个发展方向——先是见自己,然后是见他人,再然后是见世界。
我开过几场专场, 场《小鹿乱撞》,基本是在讲我自己,比如我在云南的农村出生,爷爷奶奶重男轻女这个事情是我最后专场的底;第二个专场是2019年的,叫《鹿见不平》,主要是关于我的家庭。我讲哥哥家有小孩了,一家人对小孩的态度,以及我当时的情况。当时我哥哥家生小孩,我在北京北漂,我父母的意思是我得给一个大红包比较好,但是我当时整个账上就只有2万多块钱,我在得考虑自己下个月房租要怎么办的情况下,还是包了2万块的红包。当时家里人的态度是,你在北京工作,要是不给多的话,说出去让人笑话。类似这样的事情会让你比较难过,你会想,你要不说谁会说出去,以及这个事情怎么面子那么重要。加上我又比较要强,不怎么跟家里人说在北京的情况,父母就默认我在北京混得还不错。
后面还有一个专场叫《真娘儿们》,算是我女性意识启蒙的专场。比如“真娘儿们”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听到有人说,“跟个老娘们似的”,那一瞬间我意识到,为什么爷们儿是个夸人的词,娘儿们是个骂人的词,那时我就觉得,喜剧精神要叛逆,你要想点别人没想到的东西。给那个专场取名字的时候,公司说会不会不好,看起来不文明,我说不行,我就要这个名字,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态度,我不要这个词是一个坏词。
2024年,小鹿举办婚礼期间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那个专场 挑战自我,比如我把 、卵巢、 这些词都搬了出来。因为我去做妇科检查,我觉得在医院很羞耻,没有被当作一个人看待,你在那儿叉着腿做检查,那个帘子反复被掀开,医生玩手机,聊天,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病人是很羞耻的。然后到了《女儿红》专场,我讲了月经羞耻、生育焦虑,还有一些人生的尴尬。那些专场之后,我收到很多女孩子的反馈,感觉自己经历的那些东西也被看到,被说出来,我就觉得挺开心的,好像脱口秀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很多人的各种负面情绪。
再到现在,我 的专场叫《我的中女时代》。我觉得我已经看到自己的变化了,就是我已经具备足够的喜剧能力,同样一件事情能有不同的思考,并且不同思考方向里都有不同的笑点。我已经过了非黑即白的年纪。
我现在也会讲一些大词,抽象的话题,比如不配得感,女性对野心的羞于启齿,等等。我觉得意识到问题的存在,就是成长的 步,你不一定能改变它,但是意识到它的存在,就能缓解特别多的困扰,因为我直面了这个问题。我们成长过程中,一直有一些东西规训着你,比如当你获得了成功想要骄傲的时候,就会有“骄兵必败”出现,当你失败了特别想哭的时候,你首先的(反应)是谴责自己,你有什么好难受的,你就是不够努力,你要是够努力就不会这样。就是你所有受过的教育会一直在你的身边陪着你,所以像“爱自己”“做自己”这些抽象概念一出来,很容易风靡,但其实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,就是很容易接受,以为自己真的完成了这个蜕变,其实完全不是。反正我自己是这样,还是在一个反复挣扎的过程当中。
我之前讲开放麦,讲“爱自己”这个话题,讲完一出来,一个姐姐跟我讲,她很喜欢我这个话题,觉得很有意义。她说她50岁了,才学会对自己好一点,要爱自己一点。她很认真地跟我讲,你讲的这个话题我特别有共鸣,你不要觉得笑点没有那么多,就觉得它不好,它真的很好,我当时就觉得好温暖啊。
当天汤包陪我去的开放麦,他也想听一听,因为我说这个话题太难写了。那个姐姐讲完,我就跟汤包回家了,汤包说是你朋友吗,我说不是,就是观众,他说我以为她是你的朋友,还是认识很久的那种。

小鹿与丈夫汤包。受访者供图
我一直创作力很旺盛,比如我今年会讲结婚,因为我刚结婚,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喜剧演员是不会浪费素材的,是肯定会讲的。
有一段时间,为了接触不同圈层的人,我还读了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,我觉得离开正常轨迹太久了,想接触一下不同的人,因为那些地方集中了各行各业的人。我当时还挺想把我们班上所有人都采一遍,但是后来碍于我没有那么社牛,也就没有搞这个事情。但是每跟一个人对话,就好像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比如我们班上有两个家族企业里 有钱的富二代,他俩是一起来上学的,一个24岁,一个25岁。那个男生自我介绍,说我是某某集团的谁,这位是我的夫人。当时我听到“夫人”两个字的时候一下穿越了,感觉我此生都没有听到过有人在我面前叫夫人。还有另外一个男的,他是某个公司的CEO,他讲自己大学毕业之后创业,干这个干那个,过了几年之后,还是回归家庭了。“回归家庭”这个词,感觉是形容一个人之前在外面放浪形骸,但是他说的“回归家庭”是去他爸的企业里开始帮他爸做事。
我真的人生中 次意识到我的脑子不再供段子,就是去年,潜意识的恐惧让你不再幽默了,你脑子也不调皮了,它不动了,不思考了,也不反抗,反正就是死了的状态。还好这样的感觉只持续了一段时间,只要生活正常过着,它就是在继续,你在观察,在创造。
如果说我有喜剧的能量的话,我的能量很多时候是观众给我的。有时候你真的是疲惫,真的不想去,身上每一根神经都不想去。但是最后硬是拎着自己的耳朵去到了开放麦,你发现今天居然观众还送给我一个梗,在我讲的中间,突然他的一个反应,使得我这个梗让观众笑了,借用一句歌词,“大家在这陌生冰冷的城市里,电流穿过我和你”。大家每天被工作、被生活压成这个样子,但是他来到了这里。今天晚上的开放麦,我本来想我嗓子已经累了,有点不想讲了,但是 排有一个女孩子,她一开始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的样子,到后来她笑得一直捂着肚子,她肯定是肚子疼了,但是还在笑。我觉得她应该很久没有这么笑了,因为她坐 排我能看出来,她一开始抱着手,就是一种防御姿态,也没有怎么被代入,后来她笑得好开心。也许我跟她这辈子的缘分就是今天晚上的50分钟,但是她好开心啊,我也会觉得好开心。虽然讲完嗓子疼得要死,但能让大家这么开心,我可真棒啊,会有这种感觉。
我觉得做脱口秀这个事情就是真真实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,我现在活成的样子根本不是我小时候想的样子,但它一定是最符合我的样子。
我小时候的想象是受限的,想到的就是做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,至于那个稳定工作是什么,就叫上班,朝九晚五,结婚,生子,养育下一代,在一个小地方,我对大城市都没有想象,因为我也没见过太多大城市的人。后来是看了电视剧《律政佳人》之后,才对大城市的女性有了向往,觉得我要做律师,做律师就可以这么飒,好像只有律师这个工作能承载我的这份想象。就是你小时候的想象一点点被扩大,你想象的生活方式也一点点地在改变。
我觉得我和所有做脱口秀能聊得来的朋友,都是大家一点点小的笑点就开心得要死。很多人看来我们这些人都不像大人,但同时我也不老,我不会变成那种思想顽固不化的人,我一直在成长,一直在变化。因为我觉得喜剧就是对抗严肃,人严肃经常就是因为太固化。你也不会成为老人,平静地接受一切,我们遇到一切都还在提问,还在好奇、在困惑。
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一兰
责编 刘悠翔